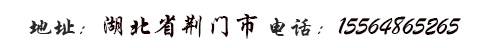冬天的蓼子花海
|
落霞孤鹜蓼子花 玉阶梅 初冬,一个晴日的上午,阳光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汁,均匀洒在一片蓼子花海上。往日水天一色的鄱阳湖床,当下远远近近皆是前来看花的人。一时间,好男如阳光,好女如颜色,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眼里的一花一草都是泼辣新鲜。 我知道蓼子花季节性很强、异常娇嫩,一旦遭逢降雨,花海便会消失。由是,一向不喜欢赶热闹的我,也来到鄱阳湖上都昌县,为的是邂逅这个花期。 在暖冬吹面微寒的风里,粉红的蓼子花似乎比樱桃花更是有情,满眼尽是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微风过去,纤柔的花草像东方的舞,起起伏伏恍若水流行云,使人顿然觉得江湖闾阎明净。 在紧邻花海的湖汊里,几头水牛正迈着步子,水像水晶般碎开。不相称的是,几只白色的水鸟或者落在牛背上,或者在水牛前面悠闲的渡着方步,一大一小倒也相安无事。天空中,大雁正迁徙而来,三只四只两只,横贯着高空。近前的一家三口席地而坐,男人环视着远山,似乎要在山的黛蓝轮廓中读出许多的心事来。女人则仰头看天,目光追逐大雁的踪迹,亦有着私情的喜悦。夫妻俩任由小孩子撒开脚丫子在花丛里奔跑,花海辽阔得让人心安。在这男女交杂的花海,空气中,似乎散发着雨后突然来访的情人肌肤的味道。其实,蓼子花并没有浓郁的清香,可是成群的蜜蜂却嗡嗡叫着,盘旋留连着不肯离去。 也许花海里最为忙碌的人要数我们这些摄影发烧友了,一个个东走西串、东张西望的样子,行迹着实有些可疑。我一面贪婪地按着快门,一面想,这蓼子花怎么就能够在鄱阳湖底蛰伏着种子,满湖的大水都淹不死它?水一退,它便年年冬天向行人烂漫地开满浅滩烟渚。这花呵,开时似欲语,谢时似有思,紧紧跟着迟日疏钟,让人只觉得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带着这个念想,我询问了当地人。一位正在修理搁浅渔船的渔民告诉我:“水蓼老一辈人叫它蓼芽菜,它的种子是随水流漂流的,只有水蓼才会在湿地上迅速生长。”也许就像太阳花、牵牛花、一串红、凤仙花、紫茉莉、鸡冠花那样,这些一年生的草本,种子很多,自己掉的种子第二年都能发芽开花。蓼子花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横走的根状茎在沙土中蔓延,进行营养繁殖,肯定具有较强的繁殖力。我不能确切地考证渔夫的答案,但我明白“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个道理,在都昌县城老港口外的印山周边、矶山湖下坝、周溪、和合等平坦的湖滩,蓼子花早已成为当地人眼中熟悉的风景,而且与他们的生活戚戚相关。蓼子花还有一个别名——半年粮,可见在那青黄不接的年代,湖边人家很多还用它来充饥的,好似藜蒿虽然是鄱阳湖的草,却也是餐桌上一道菜一样,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蔬为充,皆在情理之中。 环鄱阳湖的湖口、都昌乃至永修的吴城等地都可以看到蓼子花,这次我们是乘坐枯水期用作摆渡的渔舟来到湖心岛上赏花的,摆渡的艄公来回收费二十元,不贵但也不便宜。蓼子的花期还算长,天气好的话,据说可从10月下旬可延续到12月上旬,这么长的一个美丽的蓼子花期,定然能够给艄公带来一笔不少的收入。由此,我便想到,蓼子花是否可以与时俱进地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契机呢? 下半年鄱阳湖水干枯,多宝沙山下,中国最长的湖底古石桥——千眼 桥,从鄱阳湖水底露出了真容,如果组织游人赏候鸟,看蓼子花,观千眼桥,游江南最大沙山,游老爷庙的东方百慕大魔鬼三角洲以及朱元璋鄱湖大战十八年的战争历史遗迹,不就是都昌下半年最好的生态旅游线路吗? 在风日晴妍的天光里,前来看蓼子花,大自然有一种热闹的慷慨。只是听说今年鄱阳湖的枯水期又大幅提前了,鄱阳湖的干旱和青藏高原的积雪与冰川减少有关。如果积雪冰川的减少与地温、气温、季风环流的恶化,成为蓼子花提前盛开的先决条件,那将是怎样一个悖论? 我看不到青藏高原,那个大生态距离我们很远,可是当下看花,我还看到了花海里纵横的汽车轮胎的深深印痕,看到了许多难以消解的白色垃圾,看到花海与候鸟湿地一衣带水,看到人们“眠分白鹤草,坐占灰鹳沙”的领地纠纷。有谁能够目光炯炯地站在生态的太阳和阴影的交界处,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在花海,我发现微风吹拂的湖滩,花儿把芬芳托付给了风。越是远离人烟的地方,野花就开得越疯狂。 文图玉阶梅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odaqingyea.com/ldqyyf/7681.html
- 上一篇文章: 跟拍植物菘蓝的根,就是大名鼎鼎的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