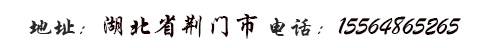又见红蓼
|
乡野的青柿与大蓼 就如一腔青涩懵懂的情怀 / 突然有一天遇上懂之的人 于是就无端的柔软甜蜜起来 文 韵秋 我们驱车在乡下的田野里。 路的两边是大块大块的稻田。新割的早稻茬里落满了觅食的山雀,呼啦啦一阵起飞,又轻飘飘树叶般落下。 大片的中稻也开始泛黄,谷粒们正滋滋的吸收着充足的日光。 野外的风里夹杂了众多奇特清新的味道。不用看,也知道哪一段的路旁是稻谷,哪一段是溪流,哪一段是在穿过一座小山垭垭。溪流边上杂生着白茅、狗尾巴草、菖蒲、苍耳子,溪流里有着柔柔的苔藓、小游鱼。小山上覆盖着青青苍苍的松木,那些松针、松果在阳光里泛着油光。各种被阳光蒸发出来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在流动的风里,有一种浓郁的铺天盖地的香。 喜欢这些活泼泼的新鲜。在城里呆得久了,便要寻找机会,也或什么也不为,只为回乡下的原野里去嗅嗅泥土的气息,访一访曾融血脉的那些亲切的草木,寻一寻渐失渐忘的人之初的情感。 有一大片特别的花在荒塘岸边,从塘埂漫生到坡底。 我远远就看见了,胡乱的惊讶起来。那凛凛然高挑的三两串红,一穗一穗的粉,细细尖尖的叶子,是红蓼没错了。它们安静的在杂草丛中微笑着,像一大片误落草莽的云霞,有一种遗世的美。 开车人停了车,容我下车走近前去细细端详。婚姻多年,他太了解我心之所往,人至中年,还是初心未改。是了,随便走到哪里,在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是花无疑。但是,对蓼花的感情,他未必能懂。 “十分秋色半蓼花”。寒露清秋,百花逐渐凋零,而蓼花却开的正好。在山野地角、圩坡渠塘,不仅独占了秋光,也是秋天的点睛之笔。它不是温室里四季可循环开放的花朵,也没有撩人的姿色,馥郁的花香。但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时,大地上指定有它的影子在认真努力的生根发芽,在阳光雨露中悄然生长。直到某天,它细嫩的花茎钻出杂草的遮掩,窜出身旁的棘藜,在猎猎秋风里,开出了一串串细碎又明丽的花朵。 我对蓼花的感情,除了它一直生长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亲切的一如邻家的叔婶姨婆,还因为,它与别的植物是与众不同的。我的外祖母没有跨过学堂大门,却识得乡间百草的药性。我们表兄姊共十几人,无论谁生了什么毒疮顽疾,被呼之为奶奶或家家(外婆)的她都能去山野采来对症的鲜草,煮了水让我们喝,或者捣碎了敷在患处。说来也奇怪,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那些草药的作用,幼时的我们极少去看医,小痛小热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有一次,我不记得是贪吃了啥,积食在心,外祖母用食指弹弹我鼓一样“咚咚”响的肚皮,遂用她秋天收集的大蓼籽煮了水,再倒些她藏在柜子深处的红糖,哄着我喝了。在乡间,红蓼的乳名是大蓼。已不记得大蓼籽的涩味,只记得那一蓝边碗甜甜的红糖水,喝了几次肚子就安妥服帖了。后翻看《中华本草》,在泱泱草药中寻找我熟悉的草木,果然见其有祛风除湿健脾消积的功效。 当凉凉的秋风扫尽了桃、梨、李、杏,等等果木上最后一片叶子,那些挂在歪脖子树上的柿子便要隆重登场了。柿子虽上不了台面,但是河里无鱼虾亦贵,整个秋天,我们便在柿子树下仰望着,驱赶着前来啄食的鸟雀。但是霜降前,枝头青中泛黄的柿子,看上去虽非常诱人味蕾,却是吃不得的,一口咬下去,嘴巴会被麻得张也张不开了。 不知道我的先祖们谁那么聪明,就发现了大蓼与青柿的秘密。 那年,我还是小姑娘时,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能结出很大果实的柿子树。秋风起时,一向粗犷的父亲竟有好耐心攀上树去,挑个大泛黄的摘些下来,把它们一颗颗装入那只肚大口小的坛子。哗哗的山溪边尽是摇曳的蓼花,拽一把洗净了拿回来封在坛口,再压上一块青石,兑上些清水,就大功告成了。过些时日,扒掉坛口的浮叶,从坛里掏出来的柿子便像被施了魔法,沙甜可口,还有一股蓼叶的清香,好吃的丢也丢不下。见我们吃的欢快,父亲也乐此不疲,一次次地摘,一坛坛地泡。 乡野的青柿与大蓼,就如一腔青涩懵懂的情怀,突然有一天遇上了懂之的人,竟无端的柔软甜蜜起来。这情景,像极了宝玉黛玉贾府初逢,只一颦一笑,眼波流转间,便两厢契合,惊醒了心底所有多情的慈悯。大自然的草木之间,草木与人之间,还有着许多神奇的不胜枚举的相生相成。所以,我以为它们,冥冥之中是与人性有着一定相通之处的,它们并非无情,只是无解罢了。 婚后有一年,我在上海,父亲院里的那棵柿子又大丰收,他知道我爱吃用大蓼泡出的青柿子,从几百里外托人带了一大袋给我,但是他忘了拔些大蓼带过来。或许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他,压根想不到这种卑微细小的植物,也不是处处都有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柿子泡好了吗?我说好了。又问: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其实我在郊外的田野里,遍寻不见蓼花的影子时,已无奈的把那袋青青的柿子丢进了垃圾箱。 家乡之于游子,总是魂牵梦萦,若细数缘由,除了父母亲人,也含房前屋后的一草一叶,含着别处无觅的红蓼花。 现在,就算给我满筐红透的柿子,我只怕也吃不下一颗。因为,它跟父亲无关,没有蓼花的清香。我深刻眷恋的,还是带着父亲掌温的柿子。或者,我总是固执的以为,柿子天生就应该有红蓼的味道。不然,食之无情,无味。 父亲的柿子树早已不知所踪了。多少次,我在老屋的院子里仔细寻觅,也找不着它曾来过的一丝丝痕迹。父亲也已弃我远去,他与他的柿子,只留在我此生有限的记忆里。疼爱我们的外祖母,亦被无涯的时光无情地带走。只有红蓼,还在季节的轮回里与我相遇,温柔又热烈的开着。 四野寂静,花穗轻抚着我欲抚摸它们的掌心,似有故人亲切的寄语传至心上。这,让我又有了些许安慰。 韵秋,一游走于生活与文字中的女子。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会员,宣城市散文家协会会员。有文散见报刊杂志及网络微刊。文学期刊编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odaqingyea.com/ldqyyf/7651.html
- 上一篇文章: 李子柒消失的55天里,18亿人被他们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