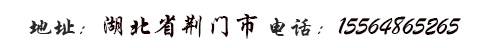再见了,老屋
|
治白癫疯办法 https://m-mip.39.net/nk/mipso_7659723.html 再见了,老屋 不出所料的话,每个人都曾搬过家,甚至有的搬过不止一次,但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老家估计就一个吧,当你和为你遮风挡雨的老屋告别,当你和与你朝夕相处的老家再见,你一定会感慨颇多,甚至会潸然泪下吧。 下午,接到父亲的电话,说老屋门窗上的玻璃被人砸碎了,里面的剩余的书本等需要处理,问我需要去老屋挑一挑有用的书吗。 我先是忿不平,怎么就把玻璃砸了呢?! 父亲说,发皮的小孩儿呗。 我心里一紧,脑补了一下老屋现在的场景:靠南的一面因为前邻拆迁,早就对外敞开了,举目断壁残垣,到处半砖碎瓦;北面矗立的五间出厦正房,正门四扇开,门东西各有一大大的推拉玻璃窗,门窗上的玻璃都被打碎,四处洞开;屋里面衣橱东倒西歪,书籍所剩无几,满地狼藉,无可立足之地;庭院里荒草过人,人屎狗遗遍地…… 下午正好学生返校,正处疫情再起的当口,我戴上口罩,做好防护,看到学生如数返校,安排班长相关事宜后,便出校门西行,远远便见拆迁完左右前邻的断壁残垣,碎瓦半砖;绿漆的大门敞开着,场院里衰草尽枯伏地,北屋的门上、窗户上的玻璃的确损坏了几块,但不是我想象中的严重,不过屋里室外也已经到处有碎玻璃了。 父亲和收破烂的老任正在忙着从西屋里成摞成捆地往外搬书,我急忙叫停,疾步向前,翻看着两位老人扔进大包里的书,心中五味杂陈——这些书都是陪伴我度过多少难忘的岁月,给我精神上的财富,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丰盈而坚实,打发了多少无聊无趣的旧时光啊!我一本一本地逐一翻看着,眼光一页一页地掠过,《名人传记》《中学语文》《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天地》《语文知识》《北京文学》《小小说》《小说月刊》《美文》《散文选刊》《读者》《意林》……林林总总,不下二十种。我抚摸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有的脸上印着我多情的吻(签名和购买日期),有的衣服上镌刻着红红的我的印章,有的穿着厚厚的棉衣,有的在衣服的夹层里藏着曾经的心语和秘密,有的在身体的心脏肺腑上留着我或家人的夜读的泪和昼读的汗……他们就是另外一个我,他们就是我可爱的孩儿们,他们就是一个个被遗弃于暗室的魂灵,他们是我(及家人)曾经注目、抚摸、亲吻和镌刻的安琪儿。我的心里酸酸的,眼里涩涩的,我知道我舍不得再次(我自年底搬上楼后,就再也没见过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了)抛弃他们,但是限于空间,且有些书或有鼠齿痕,我只能忍痛割爱了。 但是我依旧一本一本地翻看着,越是有字迹的,越舍不得丢;越是孩子用过的,越舍不得丢;越是那些当时费劲借的或用心买的,越舍不得丢;越是有照片或特别纪念的,越舍不得丢。细挑慢拣,丢了一三轮车,留下几十本。 收破烂的老任发现了一本关于二中的回忆录的书,其中有一篇王金梅老师写他的文章,他也爱若珍宝,把书从我拣留下的里面拿出来,央求我要给他,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整天以收破烂为生的、年过七旬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我见他要得切,便不好拂了他的意,竟给了他。他好像很欣喜的样子,拿着那书单独跑出屋去,单独放在三轮车的前部。我知道,这本书,准确地说,这本书里写他的那篇文章,也许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被别人载入正式出版物中,据他说,他可以季羡林、王克玉等名人同在一本书里了。而我写这篇文章,也算他又一次被人写了。 说来也巧,翻阅旧书的时候,竟然发现一本书里夹着二百元人民币,父亲和老任都惊出了声,我开玩笑地说,看吧,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点也不假吧!说不准,还能找出千八百万的存折呢! 老屋的西屋当年因为西邻建小区,挖井,造成地表下沉,导致房体裂缝,而且不止一处,朔风大的时候,贯穿老屋的裂缝股股而入,像无赖的流氓吹着锐利刺耳的口哨;屋顶的天花板,也因年久失修,掉下来好几块儿,像英勇的战士身上被子弹洞穿的弹孔,又像是年老者穿着的旧棉袄上打着的黑布丁,也像是乞丐儿被狗撵逃亡时磕掉的牙后的窟窿;满屋的陈絮旧套子,老书破本子,废弃的电线插座,坏掉的电扇、影碟机和功放机,几个大小不一的纸箱子,零星而到处都是的老鼠屎,以及风吹雨打后的潮湿和经年累月的灰尘。 我戴着口罩,手脚都小心翼翼地,轻拿轻放,生怕激起尘封多年的灰尘和回忆,生恐在不经意间邂逅曾经的旧照和日记,结果就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就在一摞摞的杂志和教案的下面,我与曾经的留言簿、老照片、日知录和日记本再次相逢,四五年的离别,一千五百个日夜的沉寂,我知道你们不会轻易忘记我,舍得离开我,正如我不会抛弃你们,出卖你们一样。 我将这些记载着我和家人流金岁月的本子一一捡起,拂去尘土,慢慢打开,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如此亲切,每一个面孔都恍如昨日,每一句话仍萦绕在耳。最可惜的是我的大学毕业时的留言簿,因为压在最下面靠地的地方,被积水浸湿,页页黏连,不能翻看,我只能将她悄悄地丢了——连同我那无限美好怅惘的青葱岁月。 父亲和老任耐心地等着我认真地挑选着,丢弃着,一趟趟地从西屋里将丢弃的书本搬到外面的三轮车上,时不时地跟我攀谈着,家长里短,陈年往事。等他们走后,我在留下的书堆里挑出五六本书——有唐朝宋朝明朝那些事儿,诸子百家和儿子小学时的日记。 围着北屋巡视了一周,外屋的书橱里的书早就被顽皮的孩子们偷卖了,估计早换了烟酒糟蹋了;当年气势辉煌的黄色布质沙发早就落上了一层灰土,甚至印上了几个黑脚印子;满地的碎玻璃碴儿,抬脚迈步都得如履薄冰。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和我曾经在这生活了十六七年的老屋最后的相见了。 老屋啊,你的东厢房里住过疼我爱我,而最后两年得了瘫痪的外公;老屋啊,你的主卧里曾经迎接过我的穿着红装的新娘子的妻;老屋啊,你的客厅里曾经爬着满屋乱转的我可爱活泼的小儿;老屋啊,你东屋火炕上曾经睡过我年过六十的父母;老屋啊,你的庭院里曾吹过春天料峭轻寒的风,落过夏天急骤漏屋的雨,响过秋天瑟瑟刷刷的落叶,铺过冬天皑皑无瑕的白雪,晒过四季清香的新洗衣服,长过高大挺拔的梧桐和青叶琼枝的小竹,养过黄白相间顽皮可爱的小狗福瑞,走过我工作伊始、新婚燕尔、初为人父、事业起步、小有所成的人生最美的韶华……想着想着,我竟然不自觉地落下泪来。老屋啊,再见了。 再见了,老屋! 等你真的被拆迁了,我又怎能与你再见? 王泽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odaqingyea.com/ldqyzz/5844.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复方大青叶片您用对了吗河北省药品监测评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