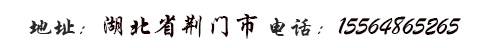崮乡的传说连载故事九
|
白癜风治疗与护理 http://m.39.net/pf/a_4346581.html 崮乡的传说(连载故事九) 星期六的中午刚吃过饭,为准备晚上迎战来访的“裕华厂”篮球队的友谊赛,民丰厂的球队就在篮球场上进行起了攻防训练。 宝义、大明、野娃仔三个皮孩跑来篮球场看球,看着看着宝义与野娃仔两个就争论了起来。宝义赞扬杰大哥、奎大哥,野娃仔推崇大辉大哥、大青大哥,两人各执己见争辩得脸红脖子粗。 球滚到场外滚出去了很远,大明追过去给捡了回来。看见笊篱坪村的同班同学小坤子打这经过,便喊他:“坤子!你去做啥子?” “我上小崮山去掀蝎子!”坤子停下脚步,高举起手里拿着的一个小圆葫芦,说:“上个星期与坡里东面蒲扇峪的那个‘工模具厂’比赛了一场,这是又要和那家赛呀?” “离咱大概有二十里地沂源县那边的‘裕华厂’,也是个三线军工厂子。”大明说。 宝义、野娃仔停止了争辩。 “咱也去吧?”宝义对野娃子说。 “没准备东西,要是也逮着了咱放哪儿?”野娃仔说。 “路上经过青岗岭食堂和单身宿舍时,捡个瓶子什么的不就得了。”大明说 “也是哈!那…镊子呢?”宝义说。 “掰个树枝我帮你做个就是了。”坤子说。 “好,走!” 宝义捡了个“蒙阴白干”空酒瓶,野娃仔拾到个“水蜜桃”玻璃罐头瓶,大明找到一个扁形铁皮的“六味地黄丸”空药盒子。坤子三下五除二很麻利、很快地用树枝就给每人做了个像镊子样的夹子。 “蝎子喜欢略微潮湿、向阳暖和面的山坡,掀石头找下面有空隙的那种掀。”坤子传授着技巧。 从小崮的西山坡一直掀到大崮西山坡,四个孩子嘴里哼唱着歌曲《打靶归来》,兴彩高烈地下山顺着厂区往回走。 厂区里的一处山坡上,一群青年男女工人正在挖山开路。举镐扬锨、推车运土,场面热火朝天。 掌钎抡大锤打炮眼的场景,格外吸引几个孩子停下脚步驻足观看。坐在地上的两手稳稳地握持着钢钎,另一人站在那里三百六十度地挥舞着一把八磅大锤。当大锤抡过头顶,随着“嘿哈”的吼声,大锤狠狠砸在了钎子顶端,发出“当”地一声响;钎尖在石头上上下跳动了一下,“嘭”地一股白烟冒起,石头粉末四下飞散。 “嘿哈!”“当!”1,“嘿哈!”“当!”2,3,4,5……孩子们在一旁数着数。一连打锤一百五十下,抡锤青年才停顿下来休息缓口气。 “休息了!”随着喊话,青年们纷纷停下了劳作,喝水的、抽烟的、说话拉呱的,三五一堆的围坐了下来。 “张哥真棒!”野娃仔凑近大汗淋漓抡大锤的青年工人,小手揉捏着他上臂隆起浑圆的肱二头肌。 张青年指着旁边正端着茶缸喝水的女青年,喘着大气:“我这一般般。抡大锤大华子姐也是很厉害的,她一气也能抡上百十来锤呐!” 掌钎青年走到野娃仔跟前,笑嘻嘻地握住了他的小手掌,野娃仔顿时疼得“嗷嗷”地叫唤了起来。 “好大的手劲啊!”野娃仔甩动着被握疼了的小手。 “小杨竟然欺负小孩子!”有个女青年调侃起哄。 “我怎么欺负他了?”杨青年乘其不备,一把抓住了女青年的手。也与握野娃仔那样,握得女青年“哎吆哎吆”直喊:“娥姐!快来救我呀!” “娥姐不就练过武功,会一些小招式。”杨青年不以为然。 “你也就敢欺负我和小孩子。敢和俺们娥姐比试比试吗?”那女青年蔑视地说了句。 杨青年两手挽袖子比划着:“比比怎么的了,我还怕她不成?” 旁边的女青年们一听都来了兴致,纷纷喊了起来:“大娥,上!”“干倒他!” “来来来!”大娥勾着带有挑衅意味的手式。 “男不跟女斗。输了是输了,赢了也是输了。”杨子笑着说。 “啊哦,小杨怕了!” “噢……怂了!” “比就比!”杨子经不住了,豁然站起身来。 一男一女两青年同时向对方冲了过去,立马支起了摔跤的架势。 一会儿大娥占了上风,杨子一个趔趄。 “杨子,加油!” 一会儿杨子占了上风,大娥差点被绊倒。 “娥姐,加油!” 山洼里顿时热闹了起来,人们的嗓子都喊哑了,几个回合下来也没分出谁胜谁负。 “比赛到此为止。虽未直接分出胜负,但从看点来说:大娥略胜!”兼职民兵连长的工会主席老刘站了出来,把大娥的一只手臂高高地举了起来。 有夸大娥的,有贬杨子的,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啊哟妈呀!”一女青年突然尖叫了起来。 “怎么了?” “蝎子!蝎子!想搬那块石头过来坐,石头底下有只大蝎子。吓死我了!” “在哪?”坤子说着走了过去,把那块石头翻了个个儿。 一只灰褐色五六厘米长的大蝎子趴在那里。扁长椭圆的躯体布满条纹,体形酷似一把小琵琶;伸张着它的两只大钳子,惊觉地高高竖起它那尖利带弯钩的大尾针。 坤子把他的小葫芦头从右手倒给了左手,右手慢慢伸向距离蝎子半尺的上方,而后猛然出手捏住蝎子的弯钩尾部,把蝎子捉了起来。接着,坤子晃动了几下左手上的小葫芦头,然后用嘴巴牙齿衔开玉米棒子芯削制的塞堵,把张牙舞爪却无法反抗的蝎子投进了葫芦里,重又把小圆口堵塞紧。 “看着怪吓人的,不怕被蛰?” “胆真大!” “没事,拿多了练出来了。还是只大老母子呐!”坤子骄傲地说:“蝎子是中药材,镇上供销社里代收代购。” “怎么个收法?”大张问。 “五块钱一斤。啊,是一市斤”坤子说。 “一斤能称多少?” “大小不均的话得近个。” “这不合计着一个才卖一分钱!”大娥惊异地说。 “要是零卖:大老母给一分,小点的两个才给一分钱,小不点的小崽子人家不收。”坤子说。 “还没注意,你们都上山去掀蝎子来?”大张看着宝义和野娃仔手里的瓶子说。 “我逮了五个。”野娃仔说。 “你看,我捉了七个。”宝义举起酒瓶。 大明晃了晃手里的小铁盒,笑着说:“我只掀出仨。坤子最多,十七八个。” “用油一炸,可好吃了,真香!”杨子舔着嘴唇。 “你就知道吃!”鼓动摔跤的女青年说。 大娥问身边背着红十字医药箱的年轻大夫:“芳姐!这蝎子有什么治病的功效?” “蝎子,具有息风止痉、解毒散结和通络止痛的功效,临床中常用于治疗惊风、中风导致的口眼歪斜、外伤引起的破伤风等病症。可以用于恶疮肿毒的治疗,还用于治疗较顽固的偏头痛、风湿痹痛等。蝎子泡酒喝,能治风湿。不过蝎子毒性很大,要慎重使用。”芳姐大夫介绍。 “清明到谷雨这段时节是掀蝎子的最好时候。为什么?蝎子趴窝一冬不吃不喝,‘毒性’最是纯正了。”坤子说了句。 “别地的蝎子六条腿,也只有沂蒙山的是八腿两钳称叫全蝎。毒性很大,蛰了会很疼的!你们还敢用手去捉?”老刘走过来关心地问。 “用镊子、夹子。”宝义展示坤子给做的简易镊子。转而又说:“不过,我还真的让蝎子蛰了一次。” “啊!”众人惊愕。 “真的!”宝义说:“那天半夜睡得正香。迷迷糊糊的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肩膀头这爬叉,下意识地用手一扑拉,就觉着像叫针猛地给扎了一下似的,一下子就给疼醒了。忙坐起来打开灯,一看,一只大蝎子就趴在枕头上,那尾巴还那一动一动地摇晃。” “床上哪来的蝎子?” “就是啊!” “难说,咱们住的房子都是干插缝垒的,只是内墙抹了层泥灰墙皮,房顶都是草苫的,没准蝎子顺墙缝,或爬上屋顶又掉落床上的呐!”芳姐大夫猜测道。 “就是!爬进来个草鞋底虫子、蝎子蚰蜒,钻进个小老鼠,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就是呀!听说,不知是哪个厂的,有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在床上睡觉还让老鼠给咬着耳朵了。” “是有这么回事!”老刘说。 宝义接着说:“半宿拉夜的厂医务室肯定没大夫。我爸先是用肥皂水给我洗了洗,又在家里找到一支小玻璃瓶的那种‘复方大青叶口服液’,让我喝一半,另一半叫我往蛰处不停的抹药水。” “那是治疗感冒的,管用吗?”老刘问道。 “刚蛰的时候,肩头火辣辣地疼得头上直冒汗。用过药后,慢慢慢慢地倒也能够忍受得了啦,不知不觉竟然还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虽是还能试着有一点点疼的感觉,蛰的地方没有肿起来,也没耽误去上学。”宝义一脸轻松、毫不在乎地描述着。 “俺们农村里叫蝎子蛰了,有用‘尿素’的,就是上在庄稼地里的一种化肥。少使点水溶化开,往蝎子蛰着的地方抹。杠子管咧!”坤子说。 “小芳,你怎么看?”老刘转向正在给一名工人处理手部轻微皮外伤的小芳姐大夫问道。 “‘复方大青叶口服液’的配方组成里有大青叶、金银花、拳参、大黄几味草药,是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大青叶主治热毒发斑、丹毒、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疮痈肿毒。金银花的功效则是清热解毒,凉散风热。拳参是清热镇惊,理湿消肿的。大黄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凉血、祛瘀、解毒等功效。”小芳大夫解释道:“蝎毒呈酸性,用碱性水中和清洗是对的。这种中草药液也许能对蝎子蛰了能起一些缓解作用,不好说!也许是与各个人的体质不同有关系,其感受、耐受、反应,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各不相同;轻者只是被蛰到的地方有个小红点,敏感的却能给蛰休克了。” “吆!捉了不少。”老刘看了看宝义和野娃仔手里的玻璃瓶,接着又拍了拍坤子的肩膀头,说道:“小伙子挺勇敢,多大了?” “十岁多了。俺们几个一般大,都是属‘鸡’的。”坤子答道。 “呵呵!怪不得逮蝎子用手捉,蝎子蛰了不疼不肿没反应。原来都是专逮蝎子吃的小公鸡呀!”青年大张开玩笑地说。 “哈哈!哈哈!”在场的都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大张!你这两天准备准备,后天‘武装押运军品’去南方的湛江港码头。”老刘给大张下派了个任务。 “哦!”大张应着。 “张大哥,湛江远吗?”大明问。 “远!在广东省。” “啊哦,再往前是不是就快到海南岛了?”宝义猜着。 “张哥又能出去开眼界了。”野娃仔说。 “哎,你们以为是出去玩,看光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好玩,押运可是个遭罪的活。今年刚过了年的正月十五,我就和大庞参加了一次押运,去了趟北方的大连港,来回统共六七天。在火车上吃的那个苦、遭的那个罪,你们可受不了!”大张说着,转身指着坐在坤子旁边正脱了鞋子倒沙子的大庞:“不信你们就去问问庞哥。” “是吗?大哥哥说说你们火车上都遇啥事了?”没出过远门,也没见过火车的坤子好奇地问。 “想知道?”大庞拉拽着站在身边的坤子,示意他坐下,说道:“好吧!那我就给你讲讲去大连路上遭遇的那些糟糕事。” 几个皮孩子围在了大庞的身边,静静地听他讲: 厂里生产的军品汽车运输时每辆车跟着一个押运人员,火车运输时每节车厢两个人。“武装押运”人员每人配备一枝56式冲锋枪和6发子弹,生活用品、食物、水等均由个人自己准备。押运的纪律要求是:一刻不离地守护,人在军品在。 大庞和大张一组,他们用5斤粮票在食堂买了50个面包,又拿饭票换了10个大馒头。 正月十五那天的凌晨,空中飘起了雪花。 四点整,运送军品的解放牌大货车准时离开了笊篱坪厂区,顶着呼啸的寒风,驶上了结了一层薄冰的山间公路。 平时蜿蜒崎岖的沙土山路本就不怎么好行驶,这种恶劣天气,驾驶员更是车速放慢百倍谨慎。雨刮器不再左右摇摆,已经结冰冻住了。鹅毛般的雪花飘打在驾驶室的前风挡玻璃上,视野仅有十几米远。爬坡轮胎常常打滑,不但不能向前行驶,反而会倒退。有时遇到急转弯道,车轮贴着悬崖路边惊险地溜过,霎时惊起一身冷汗。 也不知道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透风撒气的驾驶室内过于寒冷,驾驶员和押运员两个人的腿,时不时地瑟瑟发抖。 上午十点,载着军品弹药的车队才都陆陆续续安安全全地抵达了博山火车站的铁路货运场站,总算是结束了如履薄冰而战战兢兢的揪心路程。 由于铁路沿线受暴雪的影响,没有进站的火车车厢安排卸货装厢,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领队与场站协商后,才获准安排卸车,入了货场的仓库。 晚上六点,天完全黑了下来。 雪,愈下愈大。雪花随着凛冽的寒风,顺着仓库大门三四指宽的门缝,呼呼地吹进了仓库。 一口面包、一口凉水,两人坐在弹药箱上默默地各自吃着晚餐。 平日里货站上那种熟悉的火车进出站“咣当咣当”声响没有了,却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响声。 两人蜷缩在从家里带来的被窝里,各自想着各自心事。 大庞托着腮,望着透光的仓库大门,心想: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正好是女儿一周岁的生日,原本打算今上午去坡里,到岱崮镇上的照相馆给可爱的女儿拍张“周岁照”。遗憾恰巧安排了出差,也只好等任务完成回来再补上。厂里职工宿舍的房屋都是“干插缝”垒的,里面虽是抹有一层泥灰,还是四下漏风。有几处墙皮已经有了大裂缝,只是临时用纸塞了塞。纸掉没掉?今晚这么大的风,要是塞的纸掉了,女儿这么小,晚上睡觉肯定能冻醒的。昨儿干嘛来着?怎么不检查检查,修补一下呢?越想越懊悔,越想越生自己的气。也不知道来回翻身折腾到了几点,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邻居袁老哥家有个火炕,真好真暖和,大庞就请袁老哥来帮忙也盘了个火炕。小炕既能做饭又能取暖,一家三口吃饭、睡觉都在小炕上,既温馨又惬意。 突然,大庞的女儿从炕上掉地下了。两只小手趴在炕沿上,眯缝着小眼睛在喊“妈妈”。大庞的老婆一下子就把女儿从炕下抄起来搂在了怀里,女儿圆润小脸蛋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立刻又睡着了。 女儿骑在大庞的肚子上,小嘴咿咿呀呀地喊叫着,小手拍打着大庞就像是在骑大马,一不小心滚落到了炕底下。大庞赶忙伸手去捞,捞了两下没够着。喊了两声女儿的名字,没能听到答应。 大庞急了,猛地一下睁开了眼,歪头一看:库门大开,阳光从外面的雪地上反射了进来。 站台上积雪很厚,工人们正在清理站台及轨道上的积雪。 “做梦了?”大张望着睡眼朦胧的大庞关切地问:“听你直喊你闺女的名字。刚离开一宿就想孩子了?” “呵!”大庞似答非答地应了声,随即从弹药箱上跳到了地下,撸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焦急地一连串的问:“几点可以装车?什么时候可以发车?” “询问过铁路上调度室的值班人员,都说不知道。说是根据以往经验:这种天气,得等好几天才能装车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大张一脸无奈地说。 仓库里,大门外,站台上,焦躁的大庞一天里不停地来回往返走动。一会儿抻头往铁道尽头看看,一会儿趴铁轨上听听有没有火车行进的声音。 临近傍晚,终于盼来了一列货运的火车。冒着黑烟、喷着白雾,拖着一长串的货车车厢,慢慢地停在了货场库房前的站台轨道上。 装车、请点,一阵紧张有序地忙碌。上了车后,悬了一天的焦躁心情似乎有点放松了,押运人员们各自拿出自备的食品,开始进食晚餐。 晚上八点多,火车开动了。守护在各个车厢里的押运员们,欢呼雀跃了起来。 火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慢慢腾腾地来来回回调换着轨道加挂车皮车厢,接近十点了,也没有驶出博山站。 晚上十点半,“呜——”随着汽笛时长三秒的一声长鸣,火车“咣当”一下又开动了,并且慢慢地驶离了博山火车站的货场。 “呜!”驶过一个道口。 “呜!”驶过一座桥梁。 “呜!”与一挂客运列车交错而过。 火车的行进速度由慢及快,声音也由起先慢悠悠的“咣当!咣当!”声响,变成了急促“咣当当!咣当当!”的快节奏。 车厢厢门是百叶窗式的,火车跑的越快,灌进来的寒风就越大,身上的感觉就越冷。两人在满车厢的弹药箱上四处挪窝,寻找避风最最合适的最佳位置地方。 车门外的灯光,似如一束束的鬼火,在漆黑的夜幕中呼啸着一闪而过。 弹药箱罗列堆码的很高,火车开得越快,箱子摇摆颤动的幅度也就越大。 “睡着了吗?”大庞问了句。 “摇晃的太厉害,也太冷了。根本就睡不着!几点了?”大张抱着56式冲锋枪蜷缩在被窝里说。 大庞从被窝里伸出了手腕,打开手电筒看了一下手表:“12点多了。” “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坚持坚持吧!天亮了也许能好一些。”大张虽说是说给大庞的,也是自己这样希望的。 反正也睡不着,两人裹着被子就都坐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天南海北的聊起天来。 “年前的一个礼拜天,和汽车队的大李他们打扑克‘够级’,人手不够三缺一,大李就讲了个他听当地老乡讲的‘巴堰村’的故事。这村子在岱崮镇的南面也就几里路,不远。”大庞说。 “什么故事?”大张问。 “‘巴堰村’原来这地叫‘耙堰村’。这个村名的耙地的‘耙’字后来演变了,就变成了‘巴’字。”大庞慢慢讲起来: 此村的旁边有条大路,是远通州郡京城的驿道,距村子不远的山洼里有座寺院。过往官差行人商贩及周边附近的信男信女常到寺庙前来上香参拜,香火兴旺香烟缭绕。 有一年,一个“举子”进京赶考途经这里。不巧,遭遇狂风骤雨,遂进寺院去躲避风雨,既而顺便进香拜佛。 这个举子的舅舅在京城做侍郎官,家乡捎信说是外甥要来赶考。 殿试结束,皇榜已发布,侍郎也未曾见外甥的影儿。四处查寻近半年,渺无音讯不知下落,侍郎着实替外甥担忧。 侍郎的老家里有九十高寿老母,便借故探望老母为由,告假回乡省亲去了。 这天午时,焦阳似火罕有路人。驿道上,一路星夜兼程的侍郎一行数人奄奄蔫蔫大汗淋漓。 大路旁绿荫丛中隐约显露出寺院殿堂一角的飞檐斗拱和一段围墙墙头,一随行小伙便央求侍郎:“大人!林中有个寺院,咱们进去讨要口水喝吧!” “好的!顺便也好歇息一下。”侍郎应准。 一行几人进得古木参天的寺院,见得寺内的殿堂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可偌大的寺院却到处尘封土积、蛛网纵横,寂然无声的大殿内的香炉上也不见有香火点燃。 “怎么听着好像是有男女嘻嘻哈哈在调笑。”一随行说。 “声音不大,刚才我好像也听到了。就似京城青楼街巷传出的一样一样的。”另一随行也说。 “胡闹!佛家净地不得无礼放肆。”侍郎不高兴地喝道。 正殿上,一尊奇特的“佛”被一道高高的栅栏圈围在了里边。头发披散过肩,通身是长长的黑色皮毛。 “咦!这佛好像是流泪了啊。”侍郎十分惊讶。 “我也看到这佛好像会动弹!”一随行小伙攀爬在栅栏上探头看。 “不得攀爬!”突然有人在身后大喝。 随行小伙吓得从栅栏上摔了下来,跌坐了地上。 众人回头,五个横眉竖眼、凶神恶煞样的彪悍魁壮年轻和尚站在大殿门口。随后,一个五十开外胖胖的和尚手捻着一串佛珠走了进来:“进得本寺要守规矩,不然佛会不高兴哦!此乃活佛,曰:‘必应’佛。” “噢,就是说‘有求必应’呗!”一随行说。 “哦,这伙计是位明白人。”和尚双手合十,接着又道:“很是灵验的。走江湖做买卖的,贸达三江运通四海;求官升迁者,可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只须奉献一点点的香火钱,大功即刻有成也。施主,进得本寺有何所求?是问官运,还是盼求财运?” 侍郎瞥眼又看了一下活佛,嘴里支支吾吾应着这位和尚:“啊,路过!顺便进贵寺来看看。” “呵!我佛仁慈,你看,你与佛有缘啊!见到你,活佛都激动地流了泪,佛对你动心了。”和尚靠近了一步。 “啊!伙计们,咱还得赶路,走吧!”侍郎招呼着。 小伙计们往外走,被几个彪体和尚堵挡在了门槛里。 侍郎心里有些毛乱,慌忙从身上穿着的袍衫里摸出两锭银子,放到了栅栏前的供案上,又掏出来一大把的碎银,也放在了上边。转过身来望着手捻串珠的和尚,话音抖颤地说:“此,此次出门匆忙,下次再来定会多多带,带些香火钱。” 那和尚两眼眯着看了看案子上的银子,抖了抖手中的那串珠子,光亮的脑袋一歪:“南阿弥陀佛,施主请便!” 堵在门口的和尚让开了门路。 侍郎及随行慌忙闪出大殿,三步并作两步窜出了寺院大门,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大路上。 “俺那娘来!差点掉了匪贼窝里。”侍郎满头大汗,瘫在了地上。 一随行上气不接下气:“一进院我就觉得不对劲!” 随行小伙说:“这寺里和尚忒不简单,那‘活佛’更是有蹊跷!” “快!快快离开此处再行计策。”侍郎起身催促着。 侍郎一行急忙赶路北行,在一个名叫“坡里”的地方找了家客栈住了下来。 住下后,侍郎对那处可疑寺院暗地里私下打探走访,从而获知:原本香火旺兴的寺院自从被新来的这胖和尚掌管把持之后,这寺院就渐渐变得冷落了,香客稀少门可罗雀。这新住持倚仗与皇妃的亲戚关系,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是当地的一霸。乡民时不时地、隔三差五地就听说到周围村庄里谁谁家的大闺女丢了,哪哪家的小媳妇不见了。各阶官府睁一眼闭一眼地扯皮推诿无人管问,周边一带的老百姓告状无门叫苦连天。 侍郎回老家看过老母没待三日,即刻返身匆忙回了京城。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草木复苏。一日,皇上一时兴起,召呼了几个大臣及要员与之一同城外去踏青。恰巧这侍郎有幸也陪伴圣上去赏春郊游。 春耕时节,遍地耕牛。这边田里的老汉手扶犁把挥鞭催着老黄牛耕土,那边地里头的小伙踩在耙上扬鞭驱赶着大黑牛在耙地。皇上看得出神入化,直呼期盼上苍今年再赐给个风调雨顺,老百姓再得个五谷丰登的好收成。 侍郎看皇上心花怒放心情不错,伺机递上了写有山乡寺院住持几大罪状的诉状折子。 皇上看过侍郎递上的奏折,龙颜顿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呱哒下来了。心中思量:这和尚也太不是个东西了,祸害良家民女,残害无辜,真的是十恶不赦,可杀不可留。转而一想却有为难,这和尚是自己极为宠爱的一名妃子的大舅哥,若是杀了他,此贵妃在后宫将会特没面子。 皇上昏庸无道,手持折子倒背着手,左右徘徊踮步了两三个来回,没好气的把奏折往地上一扔,不耐烦地说道:“事已至此,遣你为钦差大臣去那乡里,就叫地方府衙出些银两安抚一下受害的乡民百姓吧!家有家规,佛有佛律,该罚该惩顺应天意。罢了,罢了!”说完竟坐上轿子起驾回宫了。 一众文武官员不知所以然,纷纷跟着扫兴的皇上返回了城里。 侍郎捡拾起折子,伫立仰天踯躅长叹:哦,佛家自有律条,朝廷官衙就不管束作恶的僧人了,老百姓就自认倒霉了?哦,仗着有皇亲国戚就可胆大妄为、胡作非为了?侍郎倒背着手原地彷徨,摇晃着脑袋嘴里如同诵经一样嘟嘟囔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知道,明道,得道,守道;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恶人不除天地不容……” 耙地的小伙驱使黑牛耙到了侍郎所在的地头,打了个转又再往回耙。地里原本大个头的坷垃土块,经铁耙上的二三十个三寸长的钉头耙过之后,成了平整细碎的土地。 看着,看着,侍郎一拍大腿,竟莫名其妙地喊了起来:“罢了——耙了!罢了——耙了!”随后就急匆匆地回城了。 进了城,直奔“大理寺”衙门府,面见了大理寺卿后直接说道:“皇上口谕下旨:山东琅琊境内寺院僧人犯下死罪。‘家有家规,佛有佛律,该罚该惩顺应天意。耙了,耙了!’当时你可也是在场的,说是要用‘耙刑’把他给耙了。咱可不得违旨渎职呀!” “‘违旨渎职’,不要命了!”原本坐在摇椅上的大理寺卿,嚯地一下站了起来:“不知晓这‘耙刑’是怎样的刑罚,‘耙’又是什么玩意的东西?” “这‘耙刑’的刑具吧,是‘耙’;就是用‘耙’把他耙了。”侍郎说得有些弯弯绕绕的。 “什么呀,耙把吧巴的!越听越拧巴,越解释越糊涂。”本是世家子弟出身的大理寺卿一脸茫然直挠头,他哪知道“耙”是农家的农具。 “嗨!给你讲吧,你也弄不明白。”侍郎故作一脸无奈且又严肃的模样。 “这样你看好不好?我派些人手给你,你这个钦差大臣同时捎带着帮忙替我兼职做个监刑官。当然,忙不会让你白帮的!”大理寺卿说着立马执笔就写文书。 “唉!没法子,谁叫咱同朝为官来,都是给圣上做事呗!”侍郎故作姿态。 惟恐有差次变数,侍郎第二天就率领着大理寺的衙门差役一干人等,马不停蹄直奔山东琅琊的沂蒙大山里去了。 到了先前那个蹊跷寺院,立刻将那些无恶不作的众多和尚全都捉拿了起来。并从寺院里的暗室里,解救出了十多个被这帮和尚们偷抢来、糟蹋了的大闺女小媳妇。大殿里的那个“活佛”抱着舅舅呜呜地大哭,哭得昏厥过去好几次。原来,侍郎的外甥进入寺院避雨,就被和尚们捆绑了起来,割掉了舌头;并且把新宰杀的狗的狗皮剥下来,糊植在了他的身上。 丧尽天良的那些和尚全都被五花大绑,押到了寺院大门外的一块地堰上的平地里。地里早已挖好了一溜两行的一个个的大深坑。愤怒的乡民上前撕打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把一个个和尚推进大坑活埋了起来,只是把他们一个个光亮的头顶露在了地面上。 老百姓牵来了四头劲牛,衙役们套起了两挂特制的带有长长铁钉的铁耙。 侍郎威严地站在地堰边上,一声令下:“行刑!” 四名差役挥动皮鞭驱赶着劲牛拉着两套铁耙,在埋到土里的和尚头上来回耙了起来。只见和尚光光的头顶上,黑红的污血喷起一尺来高。 老百姓齐声欢呼。随后,愤怒的人们手持铁锨、镢头跑进了刑场,可劲地拍打,使劲地刨砸,以解压抑已久的心头怒火。 行刑结束,百姓叩首道谢。 侍郎率领众差役回了京城,上朝面君交差。“东海杨波,皇恩浩荡。微臣遵照圣上口谕旨意:‘家有家规,佛有佛律,该罚该惩顺应天意。耙了!耙了!’将罪有应得、十恶不赦的祸害良家民女、残害无辜的佛家住持和尚,用农家平整土地的‘铁耙’就地正法,把他给‘耙’了!” 其实,在侍郎还未回到京城之前,一众恶僧就地正法之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入了京城,皇上也是早已有了耳闻。 “唉!你是真糊涂装糊涂、还是假糊涂的糊涂蛋?事已至此,乃归天意。耙了就罢了吧!”昏庸皇上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挥了几下手,示意诸位大臣都退下:“近日琐碎烦事搞得甚是头痛,朕要歇息了。” 两个人聊天拉呱也没注意时间过了多久,火车的行进速度愈来愈慢,最终“咣当”一声竟然停了下来。 天已微微发亮。 雪花从车厢厢门的飘了进来,透过百叶厢门看到外面全是一排排装着钢材、木材、闷罐及杂货的货车,隐约看出了站台上写着“兖州”两个大字的站牌。颠簸了整整一夜,在山东境地里转悠了大半圈,竟然才只是到达了兖州的铁路货运编组场站。 中午,雪继续下着。 自带水壶里的水不多了。不知停车多久,两人不敢贸然下车找地方补充。 六点多,天黑了下来,经重新挂靠编组后的火车缓缓开动出站了。 火车呼啸着经济南、德州,过天津、唐山,一路北上。越往北走越是觉得冷,两人把所有带来的棉衣、棉裤都套穿在了身上,裹着棉被相互依靠着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 突然,“呜——呜-呜-呜-”一长三短的汽笛声之后,火车急速刹车猛然停了下来。 透过百叶厢门往外看,整个旷野白雪皑皑一望无垠。 “什么情况?”大庞拉开车门探头观望。 前面车头传过来了阵阵的敲打声。 “好像是车头发生了故障!我去车头看看,顺便要点儿水喝。”大庞拿上已喝空了的军用水壶和一个大茶缸子跳下了车。 大张提醒:“小心点儿,快去快回,千万不要落下了!” 大庞从他们坐乘的车尾顶风跑到了车头,看到两位火车司机师傅正在用大铁锤,敲砸一个附着在长臂传动连杆和涂着红色油漆大车轮结合部上的一个体积巨大的冰坨子。 “怎么了?师傅!” 砸锤的师傅停了下来:“天冷气温太低了,车头排出的蒸汽在这里凝结成了个大冰疙瘩。估计今天能达零下二三十度。冰结的已经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行驶,不砸碎敲掉的话会越来越大。” “来!我帮着敲两锤。” “谢谢!不用了。你抓紧时间上车,这就快好了。” 接过另一位师傅给盛满了热水的水壶和大茶缸子,大庞顺风迅速往回跑。回到车厢,竟发现茶缸子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 “太冷了!从车头跑到车尾,热水都能结了冰。”大庞把茶缸子递给大张。 大张伸手接过茶缸,用指头戳着茶缸里的薄冰,问:“现在是到哪儿了?” “师傅说已出了‘山海关’,现在是锦州的地界,快到沈阳了。”大庞说。 “这不是到沈阳之后,还得窝回头来再去大连港?”大张跺达着双脚搓着手,嘟囔着:“东北确实是比咱山东冷大发了!这东北人冬天是咋熬的?” “人家家家有暖和和的火炕呗!”大庞说。 大约过了一刻钟,火车拉了一声长笛“呜——”,开动了。 整个车厢像个大冰窖,两人鼻孔和嘴巴呼出的热气迅速凝结成了冰霜,眉毛和胡子茬上都变成了白色。 “咱们俩不会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班长那样冻成冰雕,冻死在车厢里吧?”大庞哆哆嗦嗦地打着颤:“我们活动活动身子骨吧!不然,说不定还真能冻僵。” 两人在车厢里又是蹦又是跳的,直到身上、额头有了要出汗的意思才停下。蹦几下,跳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反反复复地活动着身子骨,不再有了寒冷的感觉。 可能是由于大量运动的缘故,大庞觉得有些饿了,就拿出挎包找吃的。 翻腾了一阵,面包没了,就拿出了个大馒头。馒头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咬不动;啃了啃,只是啃下一点点碎末末;吧嗒吧嗒嘴巴,将末末咽下去,接着把馒头转换了个角度继续啃。 突然,大庞一下子扔掉手里的馒头跳了起来,十分痛苦地捂着左边的腮帮子在那“哎哎”地打转转。 “怎么了?”大张惊问。 过了好一阵子,大庞张开嘴巴朝手掌吐了一口,然后伸给大张看:掌心上,带血的口水里有一颗牙齿。 “啊!”大张惊得两眼睁得老大。 “馒头冻得像个石头蛋,给我硌掉了一颗牙。”老庞捂着腮委屈地说。 …… 正月十八的上午8点,火车缓缓驶入了大连的火车货运场站。随后,又用汽车转运货物送到了大连海港码头。 午饭没吃的押运人员一直忙活到下午2点多,才与某军区后勤部的接收人员完成了军品货物的交接…… 大庞站了起来,一只手拍着宝义的肩头,另一只手拍着野娃仔的肩头,看着坤子说:“看着守护了4天4夜的军品慢慢离开视线,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好久。一路上遭罪的百味心情,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啊!” “当时归心似箭,哪还有心思去看大连的风光海景,只是想着坐车快点快点回家。”大张说。 “在车上一坐好几天,只要有吃有喝的还好说,那想拉屎尿尿了咋整?”坤子问。 “嗨!车门拉开个缝,直接往外呲不就得了。哦!小便可以,大便不好办!”宝义说。 “我还真的在车厢里解决了一次大便。在门口铺上一张报纸。待你提起裤子系好腰带,那屎早已冻硬了。把报纸卷巴了卷巴,拉开厢门,一脚就踢出了车外。‘嘣——嘣——嘣!’在铁道旁蹦跶了好几下。”大庞笑着说完,大伙也都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歇的差不多了吧?再活动活动,半个小时后收工!”连长招呼道。 “干活喽!”大张说着去拿大锤,没想到青年女工大华子已抢先一步把大锤抢在了手里。 大锤、钢钎、铁锨、洋镐、打夯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修路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又开始了…… (未完待续) 作者:张同俊,山东民丰机械厂职工二代,系后勤科长张岱云之子。九岁时随父迁入民丰厂,后全家又调往裕华厂。年,在泰山机械厂参加工作,年调青岛工具一厂工作至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odaqingyea.com/ldqypz/7774.html
- 上一篇文章: 草木深香,染进红尘,少林八段,锦上添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